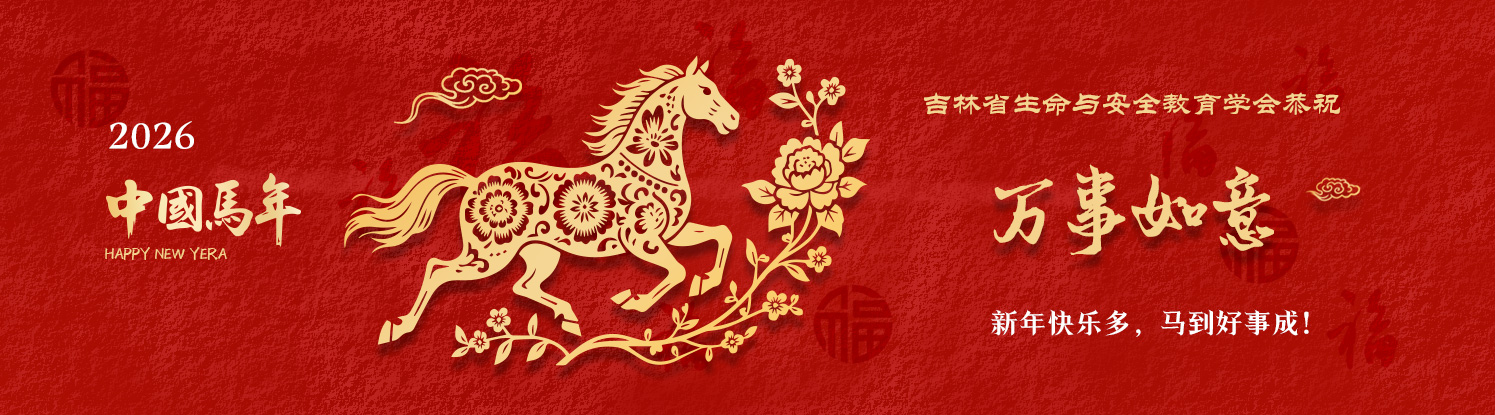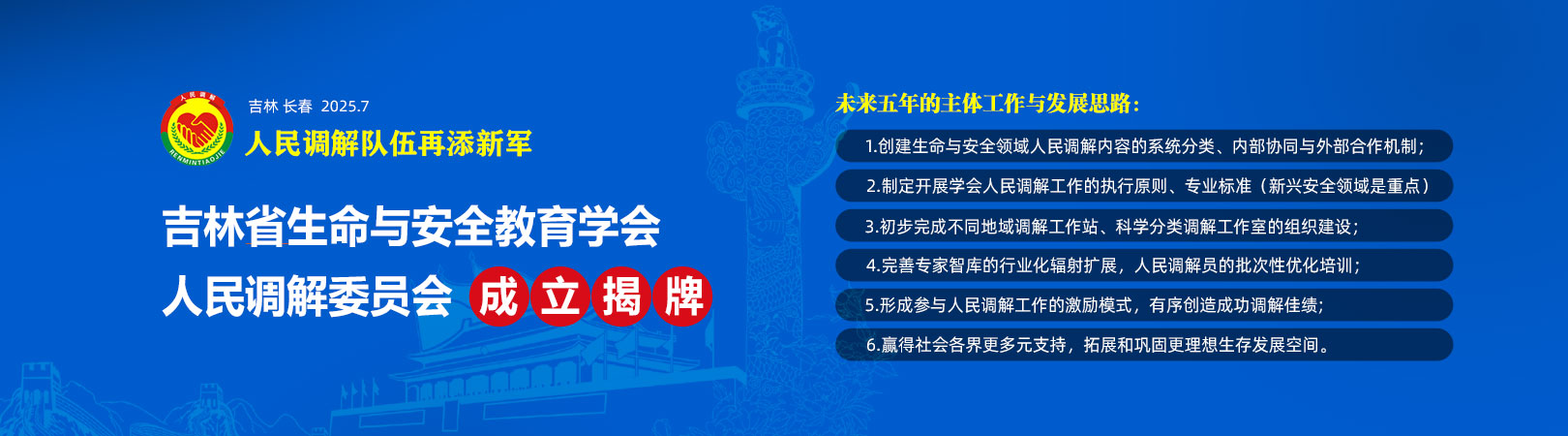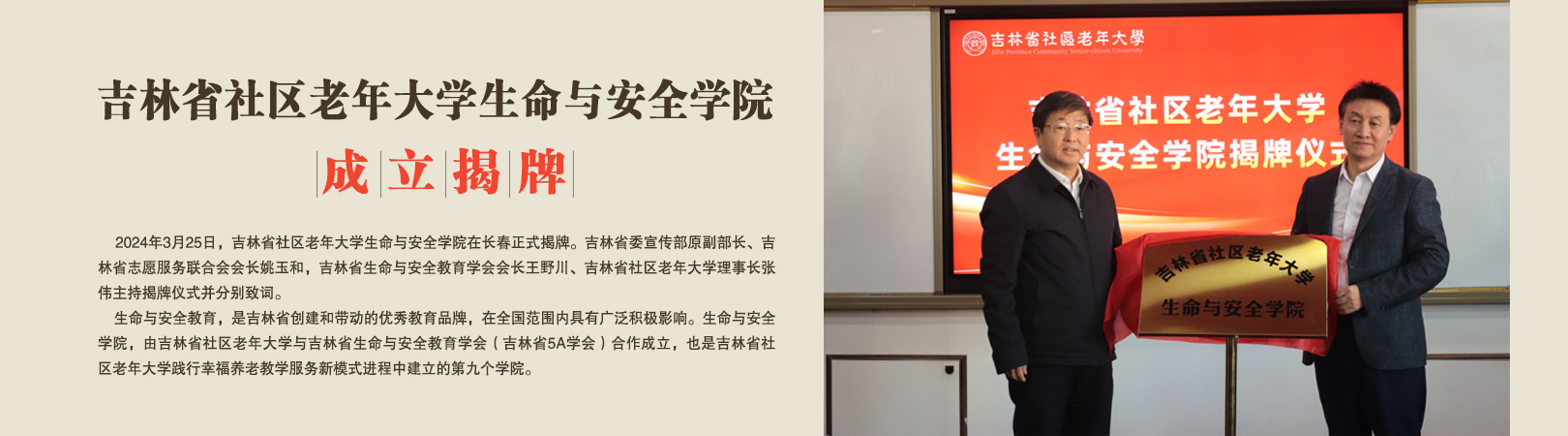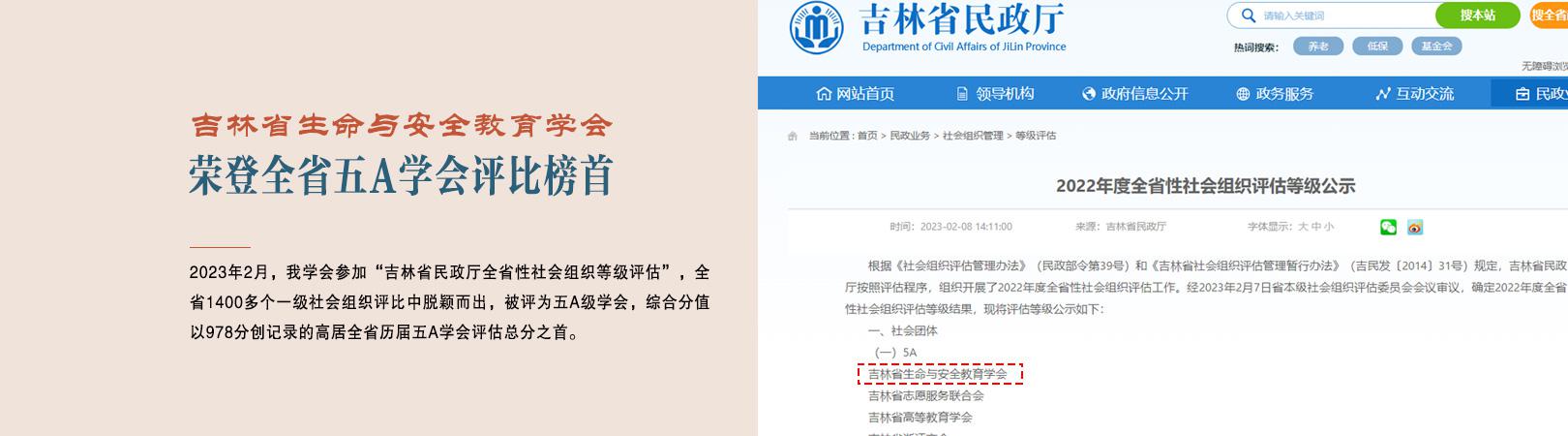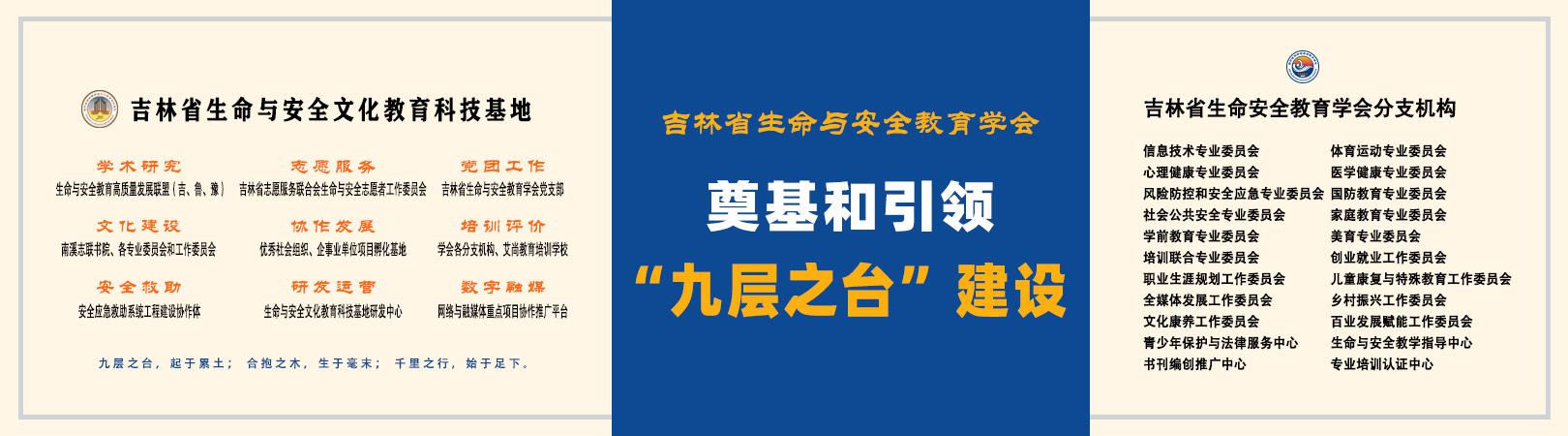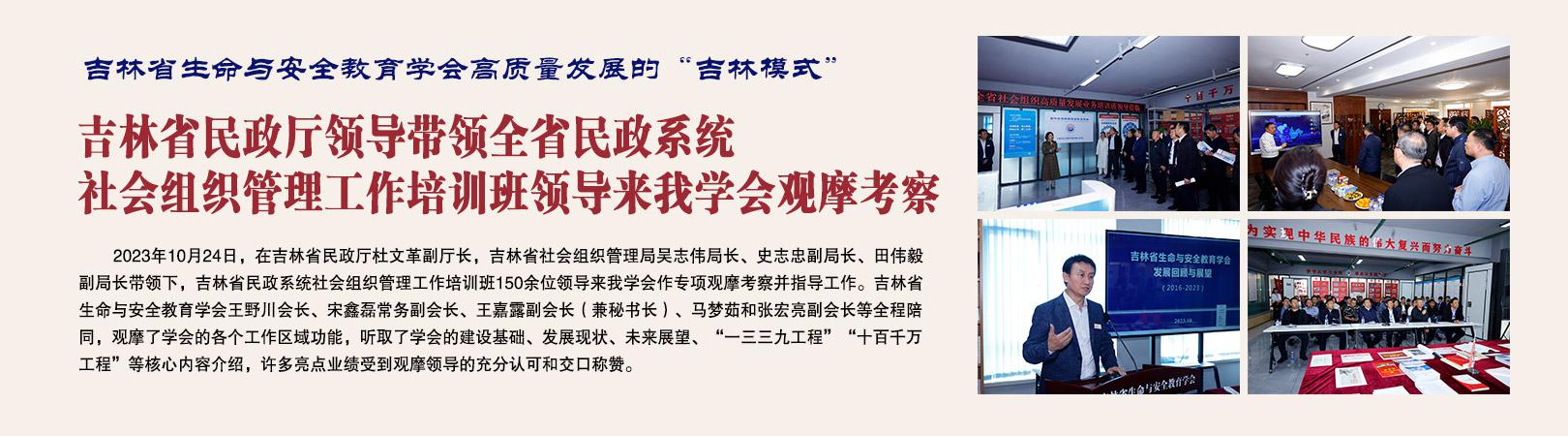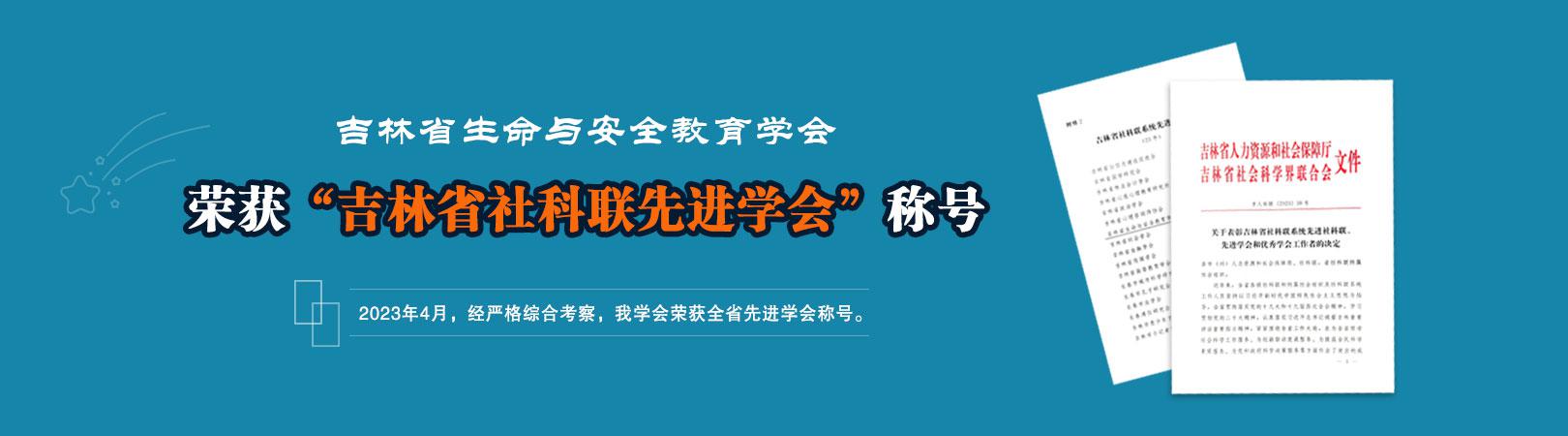生活的流程日益清晰可循,生活本身那份具体的、可感的、与人相连的质地却变得日益陌生。人类学家项飙所描述的“透明不透气”状态,正成为我们时代的普遍困境:高度系统化带来表面的“透明”,却窒息了真实连接的“透气”。正是为了回应这种深刻的“陌生化”,《你好,陌生人》这本书应运而生。
动物园的审美点在朝着“尊重差异”不断更新
贾冬婷 :我们再来问一下沈园长,我觉得红山动物园越来越成为一种现象,就是因为动物园它天然是在一个被观看的结构中存在的,但是南京的红山动物园是这两年最红、最吸睛的动物园。那么您可以谈一谈这两年红山动物园的变化吗?我们觉得这个网红化是加速了的,不知道在这过程中有什么你感到意外或者是不得不去面对的事发生?
沈志军 :我们在共创《您好,陌生人》的时候我和项老师在一起交流,这两年也的确有一些变化。比如说从动物园的大环境的变化,因为传统的动物园就是一些陌生人去参观动物、观察动物或者娱乐猎奇的一个地方,历史上,动物园的形成其实是一个文艺复兴时代之后,对待平等、对待自由的一个追求。普通人是接触不到动物园的,只有达官显贵为了凸显自己的财富、权威会搜集天下的珍禽异兽,供自己以及和自己的这种同一阶层的贵族来欣赏的。那文艺复兴之后就把这样私有的园子打开,变成了一个公共的空间,让很多陌生的人去参观另外一类非人类的生命。随着文明的发展,更多的人在追求这样的一个平等尊重,认为另外一类非人生命的,也是应该得到尊重,应该得到一个平等的对待。那一直到21 世纪,随着我们文明的发展,科学的发展,我们对待生态的这种认知也就越来越友好。不再用那种人类是万物的主宰者或者金字塔顶端的姿态去俯视任何一类生命。所以近两年我们也在思考,动物园既然在传播我们要尊重生命、敬畏自然这样的理念,这样的价值观。我们在动物园里就要做好生态的修复,比如大环境的改善,那以前我们对公园的那种审美观点是什么?
比如公园你的草坪要整齐,花坛模纹要整齐,那整齐代表着什么?代表着单一,代表着不能有差异化。你有一棵杂草在里面都不行,曾经我们在城市公园管理的时候,我们也被扣过分,因为你有杂草。那后来我也在想这是为了什么?我们红山动物园在做一个生物多样性、生物友好的一个园子。那我们就要应该允许一些不同样的生命、不同样的植物在这个环境中生存。鸟拉了一泡屎,然后隔了几个月,它带来的种子,生根发芽,长出一条草,跟原来的草坪不一样。但我们恰恰就应该尊重这样的一个差异,我们所追求的生物多样性,我们要真正地在动物园里面传递给公众这样一个理念:我们要尊重每一个生命,尊重差异化。所以这两年我们也摒弃掉过去的那种传统的园林审美,我们做森林花园。
这是大的环境,我们也在尝试改变小的环境,比如给动物模拟它野外生存的环境,在红山动物园里营造这样的一个城市家园,我们也在做这样的环境修复。传统的动物园,大家小时候去看的动物园都是铁笼子、水泥地,你几乎看不到植物的。那是他的家吗?不是,那是他的牢笼。后来我们慢慢地从牢笼式到背景式,到生态式,到现在的沉浸式去改善。那沉浸式是当前动物园最高的设计手法和水平,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动物它野外的归属地、生态地理是什么样的一个环境,给它在动物园也营造同样的一个野外的家。从植物的品种搭配,从有生命的一直到没有生命的,它所生活的环境空间从温度到湿度到光照到给它的土壤、崖壁、土坡、水系等等,都是我们给它的这个生态系统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在给小动物营造这样的环境的时候,是非常丰富的,但是大家知道小动物是有破坏性的,对植物来讲,对水体来讲,对地面的这些地表的材料来讲都是有迫害的,那就需要保育员和饲养员不断地去更新它的环境,我们叫“丰容”,增加它的环境丰富度。
“我看到那个动物在来回地走动,可能是一种刻板行为。”
这是从环境上面的这些变化。从游客端来讲这两年变化也是非常明显的。比如说从年龄结构来讲,我们以前统计 60 岁以上的老人带着1米4以下的孩子比较多。从我们的购票率来讲的话,我们以前购票率70% 多是不买票的,那也就是预示着老人和孩子比较多,那后来慢慢的因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丰富的一个游览环境和新的一些价值理念,让更多的年轻人喜欢逛动物园。现在参观动物园的人群年龄从 18 岁到 23 岁占到了16%,就是大学生这个团体,23 岁到 30 岁占到了39%,就接近 40% 了。 30 岁到 40 岁的大概是在 20% 左右。那这样的群体来逛动物园的感触是什么?他可能接触到的我们所提供的这种有效的信息,他更能吸收、更能转化、更能的让他们认同人和大自然的关系,人和另外一类非人类生命的关系。
不像以前的老人带孩子的时候,我就看到一个老奶奶带着小孙子看到红腹锦鸡说:“这个鸡真漂亮,要炖给我家孙子吃就好了。”他对动物的第一理解就是能不能吃,好不好吃、怎么吃。现在大家和另外一类生命产生的交互越来越多,有了更高的认知,这就是我们动物园的成功之处。还有就是游客的来源地,以前的游客大部分都是南京本地人,大多数人都知道每个城市都会有一个动物园,它是一个城市功能的存在,就像每个城市都会有图书馆和体育馆,它是一个公益设施,是一个公共产品。那现在红山动物园,大概 70% 是外地人,只有20%多是南京本地人。这也说明了,整个的游客量加大了。
还有就是游客的行为也在发生着变化,以前都抱着猎奇的心理去看,比如看这个动物丑,那个动物好看,用自己的审美去看动物,但现在的人都抱着一份对生命的尊重去看动物,有时去看得很专业,很多游客会在后台给我们官方的微博、微信留言。“我看到那个动物在来回地走动,可能是一种刻板行为。”我觉得这些游客都给我们提了很好的建议,因为我们饲养员这个在工作的时间,他并不是所有的时间都盯着动物去看,他要到后台去准备营养餐,去打扫卫生,去消毒,甚至给动物去做玩具等等的。所以更多的时间是游客在帮我们看,游客就会告诉我们,那个大象有点刻板,那个老虎来回踱步等等。这就提醒我们在日常的丰容管理中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那这些都是陌生的游客给我们很好的一些建议,通过他们全方位的一些观察,全时段的观察,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些行为,让我们更加科学的、专业的去照顾好动物。
那其实我们做这些事并不是奔着网红去的,这不是我们的目的,但是在我们细心地做这些事的过程中,我们得到了网友的认可。比如说我们今年上半年对全园的 12 个厕所做了男生和女生的标识的改造,把以前男性、女性等换成用不同动物的性别标识,比如说雄狮和雌狮的,雄狮有鬃毛但雌狮没有,来代表男性和女性。还有山魈,雄性的山魈的脸就像我们京剧脸谱一样的,而雌性没有。还有冠皱盔犀鸟,它的喉咙不同性别也是不一样。那我们就用这样的一些微小的改变,既有细心的表达,也做科普。没想到一个特别细心的网友,他跑遍了 12 个厕所,他把 12 个厕所的所有的男性女性的图全部传到网上去,然后让我们一下变成冲上了全国热搜第四。
这其实在传播的过程中,我觉得很多的网友是非常认同我们的,我们用了他们最不熟悉标志去标识他们最熟悉的场景,用雄狮,雄性的山啸,雌性的山啸,这样的一种表达方式,让他觉得很新奇,而且把自己的情绪价值拉满,上个厕所都觉得很开心,很愉悦。包括在前几年,我们景区里面都有那种游览观光车,车子的喇叭都是滴滴滴的,然后我就和小伙伴说,这个滴滴滴的喇叭会让走路的游客很烦躁。我说能不能有一些那种温馨的声音,让他们觉得很新颖的,我们于是就录了一段长臂猿的叫声,长臂猿唱歌,两岸猿声啼不住。
今年上半年有一个外地的游客晚上发了他的心得体会,他说:红山动物园你还有什么骚操作?你的这个游览车的声音都可以用长臂猿的歌声。所以很多人对于这样的一些温馨小创意都会觉得很有趣,会觉得我被尊重了,我的游览体验很好。包括前段时间很热,然后我们给小动物们,准备冰块、空调,在室外还给它雾森,就是喷的那些雾,然后雾化了之后会很凉爽。然后从去年开始,我们逐步地全员在推广,就是给游客的参观通道上面也做了这些雾化装置。然后有一个游客就写了:红山动物园,把我们游客跟动物一样的对待,也享受到雾森了。
所有的这些,我觉得其实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的心意是宠着游客,能够让游客有更好的体验。同时游客的一些反应其实也在强化了我们,激励我们提高我们的服务水平。那下一个十年可能要花更多的心思,不仅仅对动物好,而且还要对我们的游客好。未来我们还会面对很多的挑战。比如说很多网友,生物和生态学的知识比我们还专业。这就要求我们团队的每一位成员去研究动物的自然史、进化史,甚至野外的生活史,包括我们的生态学领域的一些科学知识,这样才可能让我们在动物园里面对待不同种类的动物时,给到它们的照顾是更科学和专业的,而且是定制化的服务,这样才能让我们动物园不仅仅在物种保护领域,还有教育领域、科研领域等的这些方面做得更加完善。搭建一个更好的给来自五湖四海的陌生的游客的一个社交平台。
与陌生人熟络的关系变成了一种知识,而不是一种处境
贾冬婷 :谢谢沈园长的这个实践,我觉得您提到的去逛动物园的这个人群的变化,包括他们的行为模式的变化,其实背后还是我觉得动物园去营造了一个更加自然生态的这种环境。因为动物园是一个人可以去通过动物的行为去投射自身,去反观自身的这样的场所,我觉得这个里面也会让我们去参观的人去反思我们的生态系统发生什么变化,包括我们怎么再去处理跟周围人的关系,也是一种学习的场所。然后我们最后一位作者,段志鹏,最近好像在广州美院是吧?参与了一些大学的课程改革,好像你推动了几门课程叫方法与实践,而且第一学期就让学生去观察陌生人,这个你可以展开讲。另外你好像在里面提到把生活当成一个项目,这个说法在大学里听上去好像挺奇怪的,也请你解释一下。
段志鹏 :谢谢贾老师,因为我差不多在做陌生人播客的时候是在读博士,然后刚好结束之后,一直在跟向老师一起做关于附近相关的事情。刚刚听老师们的对话,这让我想到之前有一个日本的社会学家叫宫台真司,他说新自由主义是什么?是一群没有经历过自由主义的记忆的可怜人的一些东西,他是用记忆去讲述那些没有体会过什么是自由主义,但是坚持着一些自由主义形式的人,他们所实践的一些东西,那是关于记忆的。我就在想记忆是,因为我是 1995 年出生的,然后某种意义上是在一个 z 时代刚开始的一个状况下,这个里面也确实是有一个关于处境跟知识的差异,是因为我意识到从我,包括我现在面对的学生是更小的一群人,他们的感知是在这种数字媒体下一点点被侵蚀的,就是你能知道自己的感觉能力、感官能力是在发生着变化的。所以刚才那李老师说的用一个就是找苹果,但是一直都在卖桃子,我觉得这是个非常好的作品,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他们是没有关于乡村的记忆的,或者说是这种好的邻里关系,这种与陌生人熟络的关系变成了一种知识,而不是一种处境,他们是在这种匮乏的状况下长大的。那在这种长大的情况下好的东西是什么?什么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好的记忆?这是一个很微妙的事情,就是因为让我想到,现在可能对于李老师来说,加缪是他的存在主义的一个知识。但是你要是看现在的二次元的作品,二次元是高度存在主义化的跟精神化的,就是它里面讨论的是关于存在的问题,关于种种这样的问题。所以我会在想他们的处境是需要自己的叙事的,是需要自己去讲述他们自己的状况,就跟项老师说的这个处境是要去看的,因为我觉得这个精神化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我去广州面对的学生是一群差不多是 2007 年到 2008 年左右出生的人。他们的初中到高中是横跨了整个疫情,那这样的就是他们的精神世界是非常之丰富的,但是又很难去认识到处境是什么,因为处境里面是有他者存在的,这让我想到生态学里面有一个叫Gipson,是一个生态学家,他说怎么区分真实跟想象,你就一直在去感知到一个东西,你可以不断地阐释它,但是真实是什么?就是你越看它越多,你越看它里面东西越丰富。
“生活作为项目”不是设定目标,而是让它成为一种可能,一种需要有意识的事情
我现在在广美参加的这个课,是一个关于他者意识的形成的一门课,这个课是广美现在在进行的一个基础课的改革,就是把所有的大一学生的通识课,比如教怎么素描全部给做一个大的改动,把美术的那些基础素描缩成了一个部分,然后来加入了一些东西,比如说用图形去回应技术的快速变化,艺术教育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在 2021 年,我作为外部人员参加了“看见最初 500 米”工作坊。这个课的意思是通过观察周围,观察广州的社会现象,作为线索去思考艺术创作该是什么样子。我们开始的线索是“眼力”——观看的力量,怎么穿透表象看到事情。课程结合了人类学的方式,像做田野,让学生去看周遭。同时我也跟踪了整个学校的改革,涉及六七十位老师和 1800 多个学生,一所中国画学院。黄叶达老师带着学生观察周遭。有学生发现书法选修课门口总有一位阿姨卖毛笔。中国画学院课程里并未特别教笔墨纸砚知识。一组学生去观察这个阿姨,看她如何知道课表、出现,发现阿姨有门路通过学生摸到每年选修课的时间地点,快速到教室门口卖毛笔。学生第一次去到阿姨的地方,知道毛笔怎么生产出来。之后,他们用阿姨的毛笔,一个字一个字地把关于阿姨的田野报告按书法格式写了下来,形成一个长手卷。这非常打动我,体现了对阿姨的关注和关怀。
另一个例子是我和陈丹老师带的实验艺术班级。一组学生对学校附近堆满过季外贸服装的店感兴趣。第一次观察后,他们提交了很长一个关于如何改进店铺的报告,比如阿姨直播不专业、留不住客户,服装没打理好等。陈丹和我建议再看看。转折点发生在他们多看一眼:发现阿姨直播时直播间只有两个人,其中一人是偷看她的。阿姨哭了,因为直播平台流量推送诡异,她买了会员也没流量。这打动了有直播经历的学生,他想起直播的孤独感——强制调动情绪假装面前有人。他开始有更多耐心看阿姨的生活,比如为何欠钱还坚持做。课程结束他去到阿姨家,发现家里非常整洁有小花园,与店铺风格不同。
回到“生活作为一个项目”。这课里学生常问:为什么要看这些人?边界感很重要——不想侵犯隐私、打扰他人生活。这种边界感有时带有自我神秘化,周围人的生活不一定需要了解。这时需要一点刻意——生活开始很顺畅,但这顺畅让人悲伤。打破顺畅需要意识调动,教育就是一种有意识,让学生刻意去看、去做,让身体有新感知。“生活作为项目”不是设定目标,而是让它成为一种可能,一种需要有意识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