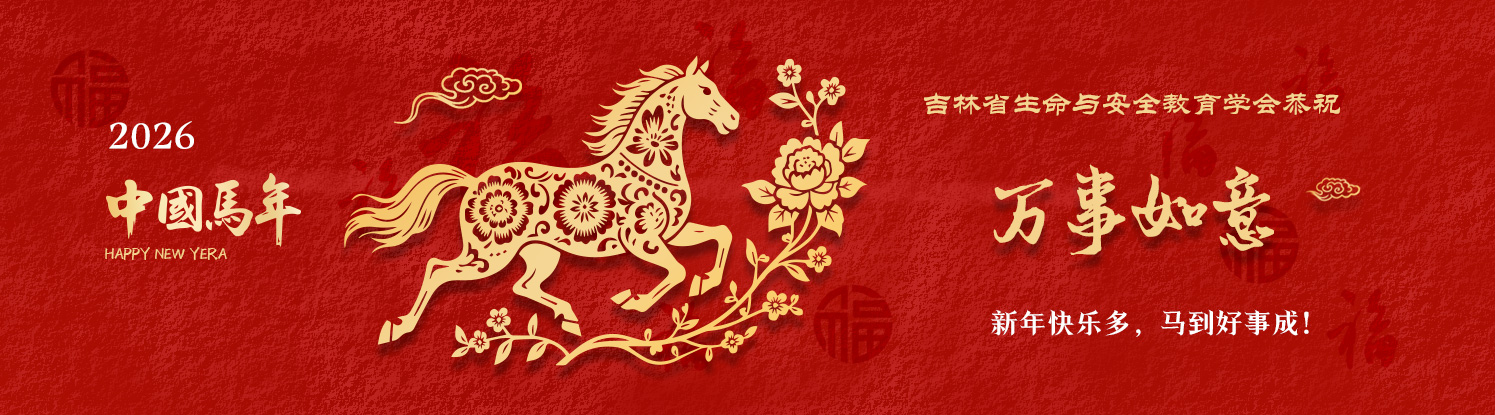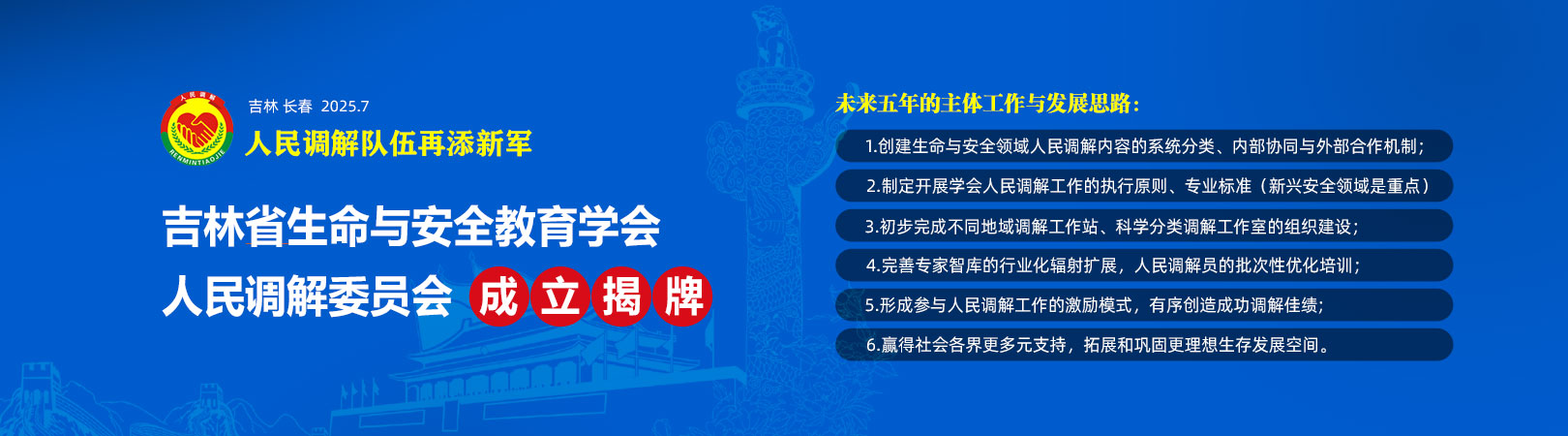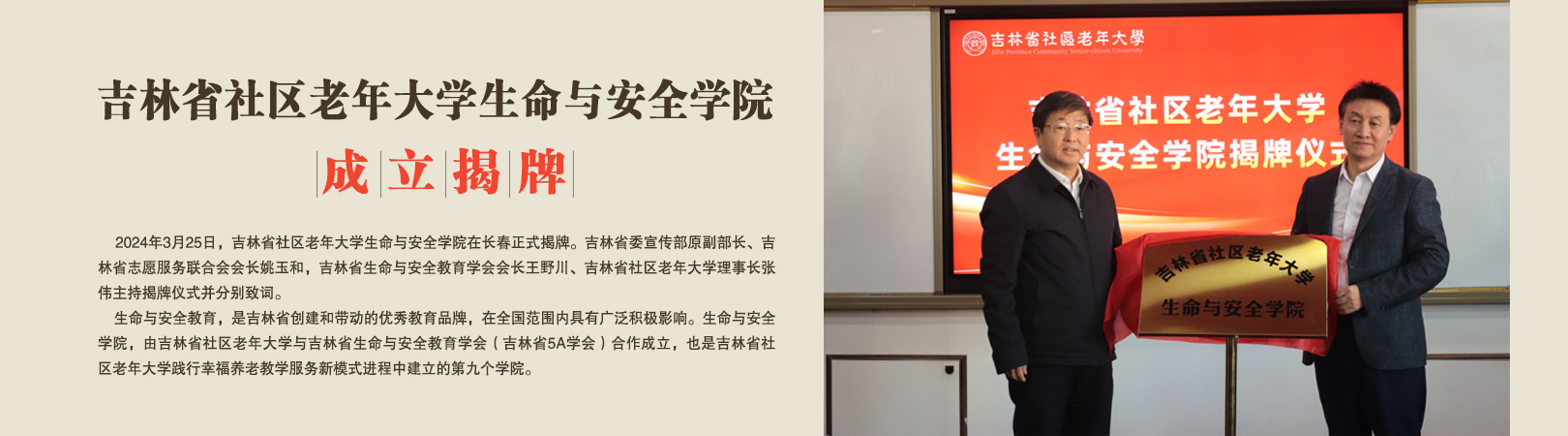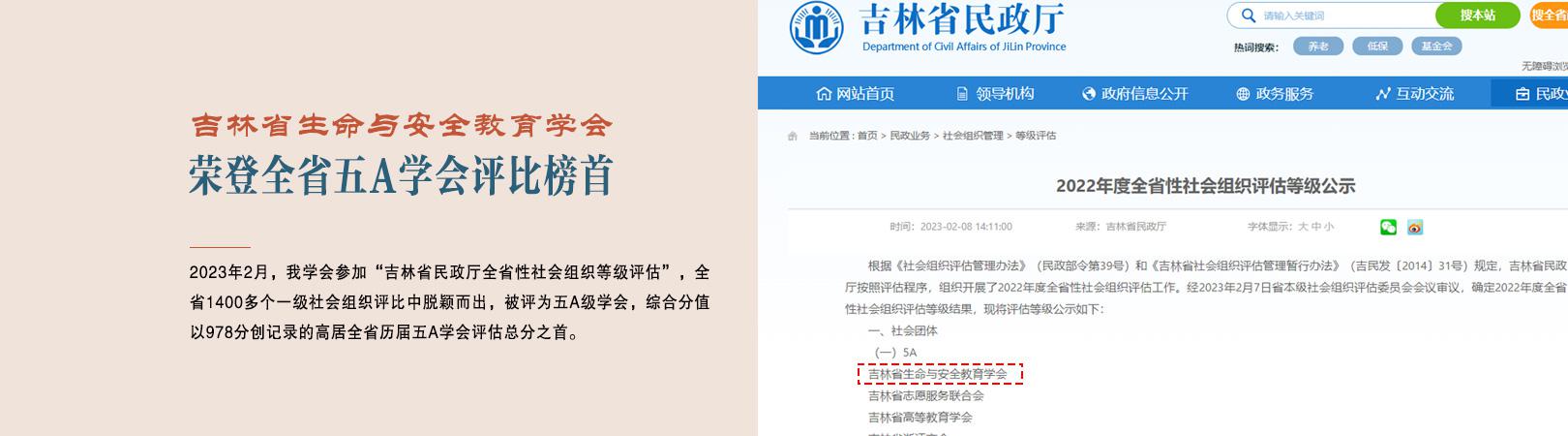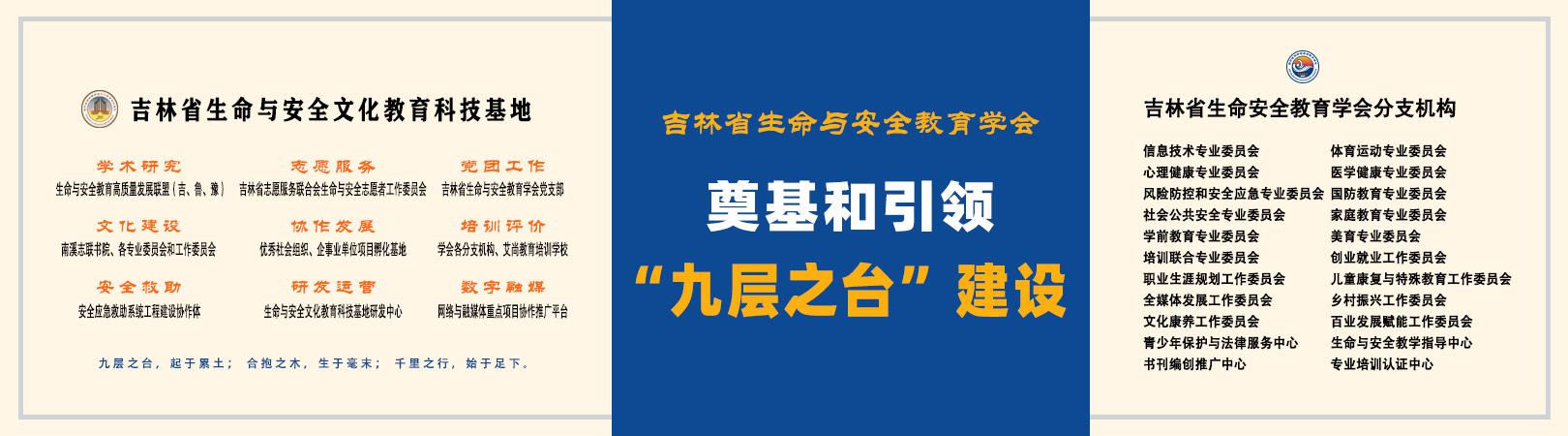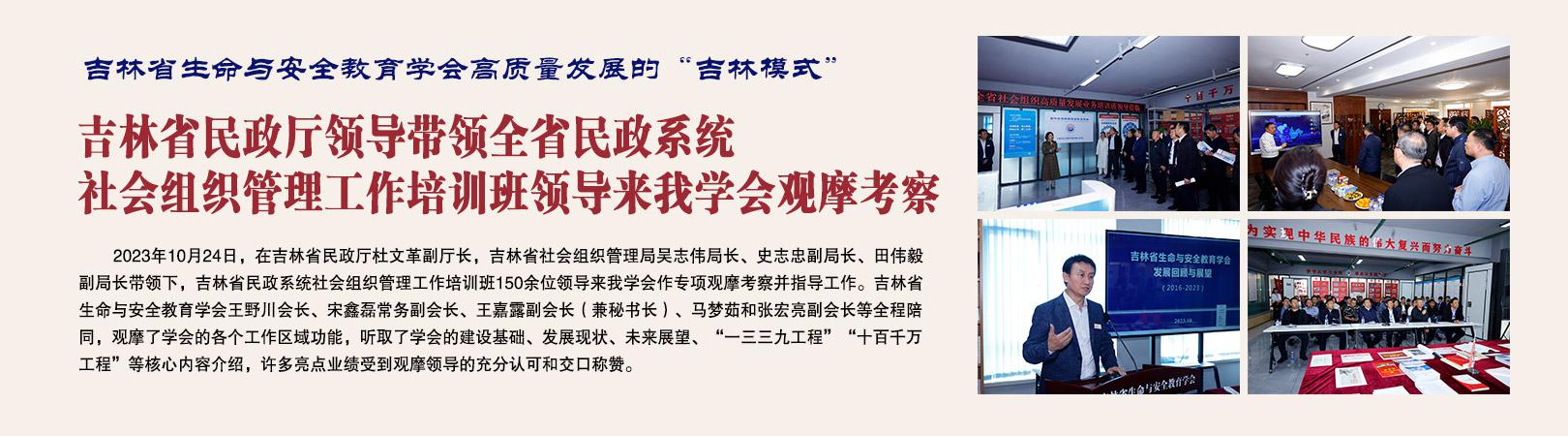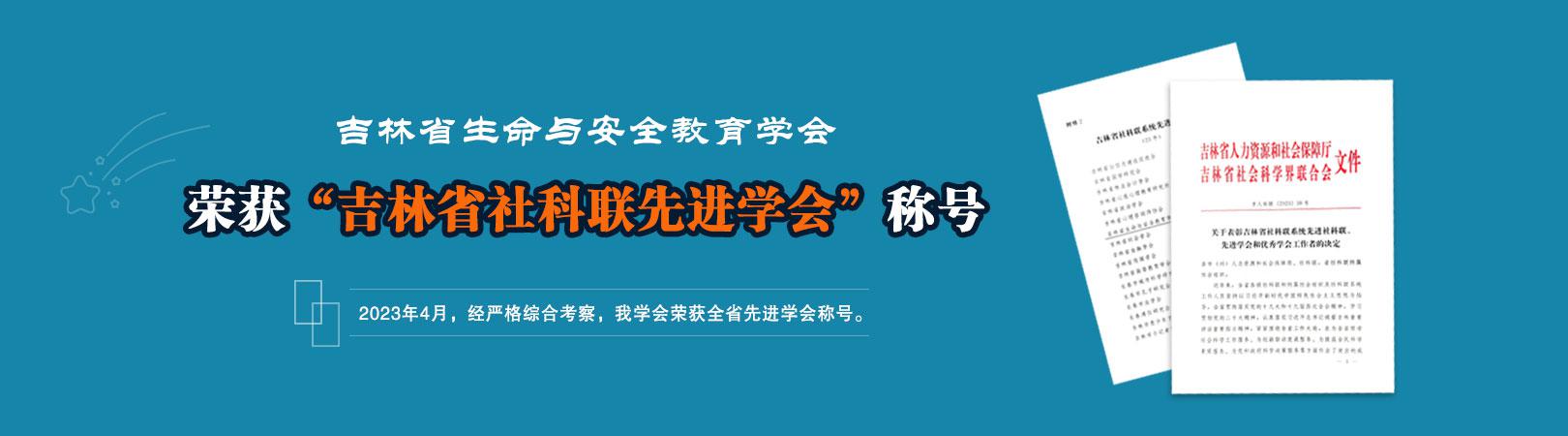近代以来,海洋作为现代文明的重要载体,被重新发现和书写。我们耳熟能详的郭沫若、郁达夫、冰心、庐隐等,均有名作问世,特别是冰心,其作品以独特的生命体验和审美创造成为海洋书写的典范。在散文集《往事》《寄小读者》、散文《海恋》《童年杂忆》等作品中,冰心对个体的海洋记忆进行文学创作,将“个人的海”融入“民族的海”,不仅突破了传统文学对海洋的边缘化认知,还在海洋书写中实现了从“海化青年”到“海的国民”的主体建构。
冰心与海洋的精神联结,源于其特殊的成长经历。福建地区拥有丰富、多元的海洋文化,与海共生已融入闽地人的血脉与基因中,出生于此的冰心自然而然地受到这种地域文化的熏陶,与海洋天然地存在着复杂的情感羁绊,后来在山东烟台海滨的成长经历,更是让她对海洋的好感与日俱增。冰心曾在散文中用“温柔而沉静”“超绝而威严”“神秘而有容”“虚怀”“广博”等形容海洋,这样的海洋塑造了她温柔、谦逊、开放、包容的性格,为她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灵感。鉴于“上下数千年,竟没有一个‘海化’的诗人”,“咏海”诗文在中国是一种缺憾,冰心与三个弟弟互相勉励:“我希望我们都做个‘海化’的青年。”(《往事·一四》)在文学创作中,冰心逐步构建起一套独特的、关于海洋的审美体系,即突破传统认知中对海洋的畏惧心理,最终升华为以海洋为精神家园的创作自觉。
海洋是冰心散文诗性精神的载体,那些书写海洋的散文无不展现着冰心独特的哲学思考。冰心经常以“海洋”为叙述和思想的基点,展开对“生死”这一宏大命题的思考,凝练出“向海而生—向海而死—万物归一”的自然生死观。于“生”而言,冰心将海洋内化为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视烟台海滨的自然景观为她生命的原点,写道:“海的西边,山的东边,我的生命树在那里萌芽生长,吸收着山风海涛。”于“死”而言,冰心将生命的消逝看作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将海洋视为生命的最终栖所,写下了“葬在海波深处”“以万顷沧波作墓田”的诗意宣言。中国古人常讲“死生有命”,于个体生命而言,总要经历诞生、成长、死亡的过程。也就是说,个体最终都要回归自然母体,出现新的个体,循环往复。显然,这种生死循环与海洋的生命循环具有同一性。冰心正是洞察到了这一生命的奥秘,才在文中表达了她独特的哲学思考。比如《回忆》一文,冰心借助“同一的我”,将她曾经见过的潭、池、江、海和“今朝的雨”联系在一起,指出其中贯穿着“同一的水”,极富哲理。这种生死循环、万物统一的观念与中国传统哲学中顺应自然、天人合一的观念相契合。由之可见,海洋已经内化为冰心生命诗学的一部分。
冰心对海洋的精神皈依,实则是一场诗性主体的文化寻根之旅。众所周知,“母爱、童真、自然”是冰心文学创作的三大核心母题,在其海洋书写中,冰心巧妙地将这三者融为一体。海洋本是自然景观,但爱海、尊海、敬海的她将海洋视为精神上的母亲。经过她的“文学编码”,海洋就成为散发着强大文学张力的“海洋母亲”。冰心自比为“海洋母亲”的孩子,写道:“海好像我的母亲……海是深阔无际,不着一字,她的爱是神秘而伟大的,我对她的爱是归心低首的。”(《寄小读者·七》)“母亲,你是大海,我只是刹那间溅跃的浪花。”(《寄小读者·二八》)至此,冰心笔下的海洋已经超越了地理空间的范畴,“海洋母亲”的隐喻具有双重指性,既指向生理母亲,又是文化母亲的精神象征。具体而言,一方面,海洋属于自然景观,通过海风、海浪以及海产、海矿的馈赠,哺育万物、维系生态平衡。另一方面,海洋象征着文化之母,“我”作为浪花归附于海洋,其终极指向实为个体对传统文化的皈依,特别是对海洋文化的认同。尽管中国古代作家长期将海洋置于边缘化的位置,但中国海洋文化历史悠久,始终承担着对外交流的职能,尤以海上丝绸之路最为典型。近代以来,《海国图志》《瀛寰志略》等重构了人们对海洋的认知,让海洋的重要性愈加凸显。当自诩为现代文明先驱的西方国家借由海洋实施殖民扩张时,知识分子对海洋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文化焦虑,郭沫若、庐隐等人在创作中开始重视海洋书写,赋予了海洋更深层次的文化内涵。此时,冰心散文中“海洋母亲”的比喻,意在呼吁个体重视和认同海洋文化,本质上是唤醒民族文化基因中潜藏的海洋性,呼唤海洋文化精神的回归。
至此,冰心通过一系列诗意的表达,不仅实现了成为“海化青年”的理想,更在此基础上对海洋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思考,开启了从“海化青年”到“海的国民”的主体建构过程,形成了“个体—海洋—国家”的叙述框架。
海军家庭出身的冰心,从小耳濡目染,深知领海和领土、领空一样重要,不容侵犯。然而令人痛心的是,晚清至“五四”时期,我国的海洋权益不断遭受侵蚀,国家海权几近丧失。在此背景下,冰心希冀于文学的教育功能,于散文中敲响了警钟:捍卫我国海洋权益迫在眉睫,此乃每一位中华儿女义不容辞的责任。
在《童年杂忆》中,冰心引述其父亲谢葆璋语重心长的话——“将来我们要夺回威海,大连,青岛,非有强大的海军不可”,把他的屈辱记忆转化为集体创伤,表达了对国家领土完整的强烈诉求。幼年的冰心能够铭记父亲的这些话,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当时新青年海洋意识的觉醒。在《海恋》中,冰心进一步指出:爱海绝不能仅仅停留在对大海自然风景的欣赏上,爱海的本质在于爱自己的人民、爱自己的土地、爱自己的国家。海洋拥有“和我们血肉相连的历史文化、风俗习惯”,与中华儿女血脉相连。因此,我们应该把她当作整个国家最重要的一部分,“依恋她,保卫她”。在此基础上,冰心又用大海象征整个国家,“愿她幸福繁荣”,并且坚定地表示:“决不忍受人家对她的欺凌侵略。”在这些作品中,冰心自觉地站在“海的国民”的立场上,回顾近代海权丧失的惨痛历史,并对国人淡漠的海洋意识发出叩问,振聋发聩,影响深远。
除了以犀利的文笔唤起国人身为“海的国民”的意识,冰心还擅长用温婉而有力的笔触勾勒海洋、表达情感,最有代表性的当数《往事(其二)·八》中“灯台”和“灯台守”两个意象的建构。灯台矗立于茫茫大海,为迷失航向的船只指引方向,时刻牵动着航海人的心,它像一面高高飘扬的旗帜,象征着“五四”启蒙精神的高扬。“灯台守”是海洋中的“光明使者”,他们必须放弃享乐,“整年整月的对着渺茫无际的海天”;从表面上看,他们只是维系着灯台的安全,实则关乎着航海事业乃至整个国家的安全,这份坚守是誓死守卫祖国海疆的精神隐喻。冰心立志把这份“为人民服务”的职业当作自己的事业,决定舍弃无忧无虑的生活,心甘情愿地去过着孤寂、清贫的生活,既承担了“海的国民”的使命,又表达了对像“灯台守”一样的奉献群体的礼赞。然而,在结尾处,冰心突然改变叙述基调,揭示了“灯台守不要女孩子”的残酷事实,与全文激昂的语调形成强烈的对比,由之产生了强大的叙述张力。写作此文时,冰心正在去国离乡的船上,几番看到太平洋(3.990, -0.04, -0.99%)上的灯台,随之联想到女性乃至国人遭受的歧视。本文固然是在回忆往事,但更多是为了启发人们的思考——性别歧视与近代中国所遭受的歧视如出一辙。冰心以女性知识分子特有的视角,将女性个体命运与国家命运置于同一坐标下,在20世纪中国海洋文学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综上所述,冰心在散文写作中,巧妙地将自然景观转化为富含象征意义的文学符号,通过海洋书写表达其生命诗学与家国情怀,丰富了中国海洋文学的书写方式,影响深远。在当今国家大力发展海洋文化的背景下,重新认识冰心的海洋书写,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